
在20世纪早期的塞内加尔,人们聚集在等待运输的花生堆中。来源:François-Edmond Fortier
花生奴隶:一个关于征服、解放和改变历史的作物的故事Jori刘易斯新出版社(2022年)
我们今天吃的花生,豆科植物的种子落花生hypogaea花生原产于南美洲,由于花生作为一种零食和油的来源而风靡全球。但与许多商品一样,它们的扩张也是一个关于征服土地和人类的故事。
在卖花生的奴隶在这本书中,环境记者乔里·刘易斯揭示了花生作物的兴起与19世纪法国殖民时期西非的奴隶制、废奴和宗教征服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为了挖掘这段历史,刘易斯仔细研究了储存在塞内加尔、冈比亚和法国的档案文件、报纸和植物手稿,以及口述历史和格里奥的歌词——西非被尊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歌手。她写道,她想讲述那些被历史书排除在外的人的故事的动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她自己的好奇心,作为一个祖先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
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和刘易斯穿越书中戏剧展开的土地时的意象,材料中的硬事实变得生动起来。她写道:“我们就像19世纪的人们一样,坐在马车里,在通往地平线的土路上嘎吱嘎吱地行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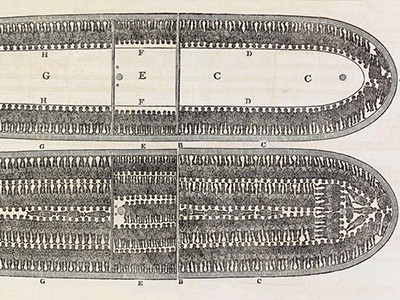
奴隶和流行病学的诞生
现代花生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生长在安第斯山脉东部的低地,由两种更古老的花生杂交而来——可能是蜜蜂偶然授粉的结果。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陆新大陆时,南美各地的人们都在种植花生。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欧洲征服者和神职人员抵达欧洲大陆,一些人带着花生植物返回,作为给皇室的礼物,等待着了解他们可以从外国获得什么商品。具体时间尚不清楚答:hypogaea传到西非,但刘易斯认为这种作物可能在16世纪末就已经在该地区蓬勃发展了。这种花生在新家的成功,要归功于当地的气候,以及农民们对另一种作物的熟悉,这种作物能在地下产生可食用的小种子:班巴拉落花生,豇豆属subterranea.
当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减少时,居住在现在塞内加尔的殖民地前哨的法国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在花生上,以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欧洲对植物油和肥皂的需求不断上升,而花生是一种低成本的资源,只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这其中的关键是免费劳动力的可用性。
法律上的漏洞
刘易斯深入研究了强大的卡约尔王国,到1850年,塞内加尔出口的大部分花生都产自这个王国。法国的花生通常是由被非洲人奴役的人种植的,尽管法国正式宣布将在其殖民地结束奴隶制。一系列的漏洞和辩解使得这种做法得以继续。例如,法国规定,如果被奴役的人被归为“家仆”或“仆人”,奴隶制是允许的。路易斯写道,19世纪晚期,法国官员曾写信给他们在欧洲的上级,讨论“俘虏的微妙问题”。一位官员警告说:“如果你阻止向殖民地供应这些俘虏,你将在短时间内摧毁各地的农业。”他荒唐地争辩说,被俘的人是自愿做奴隶的,给他们自由是“不人道的”。

全球大饥荒:大食品内部
为了满足人们对花生的渴望,法国推翻了不服从其要求的领导人。当卡约尔的非洲统治者干涉欧洲人修建一条穿过该地区出口花生的铁路的计划时,法国军队猛烈入侵。在烧毁村庄后,军队发布了一条命令,称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在你们中间开展一项伟大的文明工作”。一位上尉写信给他的母亲,描述了一个黑人是如何在军队放火烧他的家时被烧死的。即使在一些最黑暗的段落中,读者也能在刘易斯的散文中找到宽慰。她想象着入侵部队看到的景象:“雨季过后,景观和植被如此繁茂,猴面包树和橡胶树的森林,高耸的仙人掌,亮绿色的罗望子,上面挂着一簇簇铁锈色的下垂果实,还有艳丽的树木开着火红的花。”
争取自由
为了寻求自由,许多被奴役的人从卡约尔和其他内陆地区逃到法国在圣路易斯的殖民前哨,圣路易斯是塞内加尔河口的一系列小岛。在这里,殖民地政府不得不摆出支持废奴的样子。但刘易斯写道,这是一个“虚假的应许之地”,因为如果逃亡者不能在圣路易斯定居,他们就会被交还给俘虏他们的人。其中一种方法是找到沃尔特·塞缪尔·泰勒,他是巴黎福音传教士协会为数不多的非洲牧师之一,他经营着一个逃犯收容所。刘易斯讲述了穆萨Sidibé的故事,泰勒把这个年轻人藏了起来,直到三个月的居留期结束,他才能拿到宣布自己自由的文件。书中复制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证明Sidibé“能够拥有自己”。

开普敦大学解决种族主义遗留问题的斗争
泰勒将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与他作为传教士的目标结合起来。在1878年法国福音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听众,给予非洲人自由将使教会在与试图赢得人心的穆斯林的竞争中具有优势。他还警告说,贬低非洲文化的种族主义传教方式正在疏远人们。换句话说,如果能尊重人们的生命,对灵魂的追求就会更成功。
尽管如此,泰勒并没有过多地提及卡约尔和其他花生产区的奴隶制——至少档案中保留了这一点。也许这样的宣传似乎不值得冒险,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受到一些欧洲人在福音传教中的威胁。但我们无法了解他的情绪,因为正如刘易斯提醒我们的那样,历史的完整取决于遗留下来的东西。
卖花生的奴隶是对农业和西非历史的宝贵补充。但这本书对我来说,部分原因是刘易斯在塞内加尔追溯这段历史的旅程,她在这个国家已经居住了十多年。当档案中没有耕种土地的人的声音时,她就去寻找故事,向长者询问前人消失的记忆。即使她空手而来,读者也会因为她的问题而更加丰富。

 全球大饥荒:大食品内部
全球大饥荒:大食品内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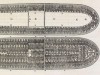 奴隶和流行病学的诞生
奴隶和流行病学的诞生 开普敦大学解决种族主义遗留问题的斗争
开普敦大学解决种族主义遗留问题的斗争 热爱土壤的小说家
热爱土壤的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