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致病性威胁,如COVID-19,难以预测。许多科学家确实警告说,一场大流行最终会来到我们面前,但它的时间和确切形式尚不清楚。即便如此,多种疫苗还是以极快的速度开发和部署,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前所未有的资金和多年的基础疫苗研究。相比之下,耐抗生素细菌所带来的具体而广泛的危险,早在我们拥有药物本身的时候就已经为人所知并有所预期。
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1945年的诺贝尔奖演讲中警告过这一点,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警告被证明非常有先见之明。2019年,耐抗生素感染为造成全球近130万人死亡——比艾滋病毒或疟疾都多。除非采取重大行动,否则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达到每年1000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数据表明,由于各种原因,COVID-19加剧了这一问题,包括大流行早期广泛过度使用抗生素。
这可能很容易让人从科学家开发和部署COVID-19疫苗的速度并假设一种新的小分子抗生素可以在全球超级细菌突发事件发生后同样迅速地交付使用,但这将是一个错误。有两个关键的区别值得强调。

自然指数2022生物医学
首先,在COVID-19疫苗之前,疫苗学有数十年的持续资助。尽管最近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和早期抗生素开发的研究进行了投资,包括“抗抗生素耐药细菌生物制药加速器”(CARB-X)和“抗抗生素耐药性行动基金”等国际倡议,但与COVID-19到来之前对疫苗研究的投资水平相比,这些投资相形见绌。
第二,现有的疫苗专门知识和基础设施能够在后勤方面迅速动员起来。相反,几乎没有大型制药公司仍在从事抗生素研发——大多数公司由于盈利能力差而停止了抗生素工作。能够立即在世界各地提供多种疫苗的资源对于抗生素根本不存在。
多年来,正在开发的抗生素储备一直不足且停滞不前。自发现一类新的抗生素以来,已经过去了近40年,目前全世界正在研发的抗生素不到50种,而用于治疗癌症等疾病的药物有1000多种。根据皮尤中心的最新评估,在这些候选抗生素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作用机制是全新的,而这正是克服日益增长的耐药性所需要的。考虑到这一点,情况就更糟了。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不是一个可以迅速弥补的创新赤字。从历史上看,开发一种新的抗生素花费了10-15年和13亿美元。
没有一项单一的政策可以让世界准备好与新的超级细菌作斗争,但我们现在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我们需要修复破损的抗生素市场;制药公司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从事创造新抗生素所需的昂贵的研究和开发。改变我们为这些药物支付的方式——将抗生素收入与销售脱钩,而是将其与公共卫生价值联系起来——是关键。向美国国会提出的两党开创性抗菌素订阅以结束耐药性上升(PASTEUR)法案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即向提供创新的高优先级抗生素的公司提供大量前期资金承诺。这些承诺将取决于新药在对抗构成最紧迫威胁的耐药细菌方面的有效性,而不是取决于售出的处方数量。这种方法为公司提供了重新参与该领域所需的稳定投资回报,同时支持对保持有效性所必需的新抗生素进行负责任的管理。其他国家,如拥有“Netflix”模式的英国,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按订阅而不是按使用次数为新抗生素付费。
随着耐抗生素超级细菌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和紧迫,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需要立即启动像巴斯德法案这样的常识和两党解决方案,国际社会必须同时努力增加关注、资金和行动,与利害关系的规模相称。


 生物医学的突破已经到来
生物医学的突破已经到来 基因疗法如何走出“黑暗时代”
基因疗法如何走出“黑暗时代” 大流行时代生物医学科学的兴衰
大流行时代生物医学科学的兴衰 对抗抗菌素耐药性的三种方法
对抗抗菌素耐药性的三种方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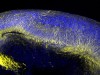 类器官为生物医学的进步开辟了新的道路
类器官为生物医学的进步开辟了新的道路 挑战抗癌药物的高剂量模式
挑战抗癌药物的高剂量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