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脱欧公投到本周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这几个月对科学家来说是动荡的时期,而且没有任何平静的迹象。

当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去年6月23日,该决定引发了一段时间强烈的自我反省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一个与非洲大陆有着强大而长期的金融和社会联系的研究团体来说。对科学基金的担忧,居留权甚至大约种族主义攻击在全国的实验室里生根发芽。
但这次投票也标志着一场虚假战争的开始: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或言论,直到它触发了欧盟管理条约中之前模糊的“第50条”条款,启动了正式的脱欧程序(参见“缓慢的离婚”)。3月29日,特蕾莎·梅(Theresa May)就会这么做。自然采访了8位被“脱欧”公投改变了生活的人,看看他们的经历能告诉我们英国脱欧后科学将如何发展。
西蒙Immler:我搬到英国,尽管伊恩·查普曼Brexit:我花一半的时间处理Brexit Gerry Gilmore:我可能的工作,但是我担心的是下一代Jernej Ule:我可能离开英国,如果我有马里诺Zerial:德国,资金在哪里好安娜斯凯夫:剩下的不确定性Mike高尔斯华绥:科学家需要提供他们的愿景Brexit多米尼克Shellard:现在不是学者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
尽管脱欧,我还是要搬去英国
Simone Immler,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化生物学家
去年6月10日,伊姆勒面试了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在英国诺维奇的东安格利亚大学(UEA)研究性进化的永久职位。伊姆勒是瑞士人,她的丈夫是以色列人,两人都在乌普萨拉大学管理实验室,但东安格利亚大学在他们面前摆着两个职位。
两周后,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我们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伊姆勒回忆道。但在英国的朋友向她保证,英国仍然欢迎移民后,她和她的丈夫、进化生物学家阿列克谢·马克拉科夫(Alexei Maklakov)决定迈出这一步。他们一家本月搬到了英国。
尽管第50条谈判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但伊姆勒持“半杯水满”的观点。她希望英国能效仿非欧盟国家以色列,向欧洲研究理事会等资助机构提供资金,她和她的丈夫都从该机构获得支持。她将在乌普萨拉继续维持一年的实验室,以便研究生和博士后可以在那里继续他们的项目。但作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前博士后,她知道在欧洲自由流动的好处,她担心自己将很难从大量年轻科学家中吸引研究生和博士后。
“我总体上是乐观的,”伊姆勒说。“要让我们再次离开,就必须采取极端措施。对于非英国人来说,在英国的生活将变得非常困难,而我们希望离这一步还很远。”
我一半的时间都在处理脱欧问题
伊恩查普曼,首席执行官,卡勒姆核聚变能源中心,阿宾顿,英国

在英国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的第二天早上,当英国国家聚变能源研究实验室的其他工作人员茫然地走来走去时,查普曼正在匆忙制定计划。该中心是由欧盟资助的联合欧洲环面(JET)的主办单位。几天后,他接受了该中心负责人的面试,而该中心的未来突然变得悬而未决。他说:“我为我想说的事情做了大量的准备,然后我不得不马上把它们都撕掉,重新开始。”
查普曼得到了这份工作。他现在的任务是带领JET度过混乱,并管理大约550名易激动的员工。这位物理学家估计,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处理英国脱欧的影响。
他的主要目标是在2018年12月目前的合同结束后,保持JET -一个拥有核聚变能量世界纪录的设施-继续运行。另一个是维持英国在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ITER)的参与,JET是该反应堆的试验台。今年1月,这两项任务都变得更加困难,当时英国政府宣布,作为英国退出欧盟的一部分,它还将退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该机构负责分配欧盟核聚变资金,并管理英国在ITER的成员资格。
查普曼说,这个决定并不完全出人意料。但它没有任何警告,也没有明确的计划,说明英国在退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后如何维持核聚变项目。查普曼现在正在收集数据,以帮助政府弄清各种前进方式的影响,包括成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准成员,以及资助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
他还通过安抚员工的神经来打发时间。JET的科学家正在准备2019年对ITER最终将使用的燃料混合进行彩排,这应该会看到JET打破自己的聚变记录——但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延长JET合同的例行谈判陷入僵局。
查普曼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没有引发大规模离职,但一些高层员工已经接受了其他公司的职位,候选人以对JET未来的质疑为由拒绝了工作邀请。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查普曼认为政府明白什么是利害攸关的,并表示它一直在做出回应。但是英国的核聚变界需要政府发出一个具体的信号,而且要尽快。查普曼说:“有一个时间窗口,过了这个时间窗口,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加剧,我们的产能就会开始大出血。”“这将对我们这个组织和整个核聚变社区造成巨大的破坏。”
我可能失业了,但我担心的是下一代
Gerry Gilmore,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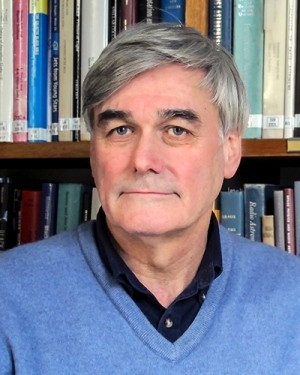
英国脱欧很可能会让吉尔摩失去他的一份工作。作为欧盟光学红外天文协调网络Opticon的科学协调员,他计划将该中心的控制权交给一个欧盟成员国的机构。
“这甚至不是我们做出决定的问题,”他说。“英国政府做出了这个决定。现在,英国协调的所有拨款都必须离开。”
Opticon为欧洲各地的科学家提供望远镜时间,并开发望远镜技术,包括实时观测、电子控制和超高速相机。由于该财团是由欧盟资助的,吉尔莫担心英国将失去在竞争领域保持领先所需的人才。
Opticon还帮助制定了基于望远镜的研究和整个欧盟基础设施的长期战略议程,Gilmore担心英国很快就会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
由于英国脱欧,Gilmore的欧洲研究委员会拨款也岌岌可危,但他主要担心的是年轻的研究人员。他担心,下一代英国科学家将不得不在一个大大削弱的环境中塑造自己的职业生涯,欧洲研究人员也会如此,他们可能会失去进入英国大学的机会。
如果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研究资助计划“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未能达成协议,剑桥等大学也将失去资金。Opticon仅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就从欧盟获得了850万欧元(920万美元)。Gilmore说,即使英国政府增加国家研究经费以弥补欧洲项目的损失,这也永远无法取代英国科学家从与欧洲同事合作中获得的灵感。
“这很简单——如果英国离开欧盟,它的科学家就会离开,”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如果有必要,我可能会离开英国
Jernej Ule,分子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伦敦

今年晚些时候,Ule的实验室将迎来一个罕见的标本——一个英国人。他的团队其他成员来自瑞士、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Ule是斯洛文尼亚公民,已经在英国生活了10年。“我的身份是欧洲人,不是斯洛文尼亚人,也不是英国人,”他说。“我不想选择国家——这对我的工作方式来说太狭隘了。”
去年8月,Ule的团队是第一批搬进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人之一,一个崭新的耗资7亿英镑(8.8亿美元)的超级实验室在伦敦市中心。乌尔说,研究人员上班时仍然会感到兴奋,但“当谈到英国脱欧时,谈话就变得有点沮丧了。”
英国脱欧对流动自由的威胁是实验室里的一个热门话题,继续获得欧盟资金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该小组一半的资金来自欧洲研究委员会,Ule担心如果英国在脱欧后失去欧盟研究资金,将会造成财政打击。但即使国家资助者弥补了损失的现金Ule说,与欧洲顶级研究人员争夺欧盟资助也有助于该实验室保持领先地位。他说:“国家资助机构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二好,只要你是全英国最好的就行。”
Ule不打算离开英国,但他说,如果“硬脱欧”——可能会让欧盟公民无法轻易进出英国——限制了他认为他的实验室所代表的开放性,情况可能会改变。“如果这违背了我的原则,那么我会考虑去别的地方。”
来德国吧,那里资金充裕
Marino Zerial,德国德累斯顿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所长

泽里尔预测,英国脱欧可能是欧洲研究的福音,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英国对做研究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会考虑欧洲大陆的国家——尤其是德国,那里的资金非常好。”
德国的研发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是欧洲最高的。
泽里尔预计,他的研究所与德累斯顿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resden)合办的大型国际研究生院的申请人数将会增加,博士后和组长职位的申请人数也会增加。“这对我们有好处。”
但他说,从长远来看,英国脱欧将损害欧洲科学。“当你失去了像英国这样的欧洲科学景观的重要部分时,它会使欧洲共同体变得更弱。”
他担心,在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研究机构合作研究的资助机会可能会减少,而剩下的机会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官僚主义。他说:“欧盟的资金无论有什么弱点,都支持了大量的项目,而且欧盟非常珍视相关的合作。”
我们剩下的只有不确定性
安娜·斯凯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斯凯夫说:“现在人们对待你的方式不同了。自脱欧公投以来,她的欧洲同事一直对开始新的合作持谨慎态度,因为目前与英国公民的潜在项目存在不确定性。
这种谨慎延伸到双方。斯凯夫和她的同事对参与欧盟的提案呼吁持犹豫态度。她担心自己可能会成为同事们申请地平线2020计划的累赘,因为有一家英国机构加入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她说:“那将是最糟糕的事情——看到一个项目失败,还担心自己可能要为此负责。”
英国脱欧是斯凯夫所在部门经常讨论的话题,该部门与许多欧洲组织密切合作,包括位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和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阵列(Atacama Large mm Array),后者是一个主要由欧洲南方天文台(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运营的国际设施。由于无法获得欧盟资金和欧洲同行的专业知识,Scaife担心英国将在未来的项目中被边缘化。“我们的网络,我们的联系人将继续能够合作。我们剩下的只有不确定性。”
但最让斯凯夫伤心的是,他看到欧洲同事在英国家中感到不受欢迎。她说,大曼彻斯特的一些地区以很大的优势投票“脱欧”,自公投以来,许多国际研究人员都受到了反欧洲和反移民的辱骂。“这些人为我们国家的智力资本做出了贡献,所以很难理解这种敌意。同事们对此感到非常痛苦。”
斯凯夫认为,英国政府的额外支出可以弥补欧盟资金的不足,以及英国好客文化的丧失,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她说,合作是推动国家创意机器的润滑剂。她警告说,如果不能接触到最聪明的人,如果不能为欧洲科学家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英国正在玩一场危险的孤立主义游戏。
科学家们需要提出他们对英国脱欧的看法
Mike Galsworthy是欧盟科学家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在英国脱欧公投的当晚,高尔斯沃西观看了“英国留在欧洲更强大”竞选活动作战室的结果。作为一名前研究政策分析师,高尔斯沃西与人共同创立了“科学家支持欧盟”组织,以确保科学家的声音在说服英国人投票“留欧”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高尔斯沃西说,当他在午夜左右从电视采访中回来时,在投票结果开始转向支持英国脱欧之后,人们的情绪明显变得更加悲观,“而且一直如此”。
高尔斯沃西是欧盟科学家的全职工作人员,他已经为这个结果做好了准备。“我主要关心的是记录这对英国科学界意味着什么,”他说。在几周内,科学家为欧盟收集了来自研究界的400多份投诉:基础设施和招聘冻结,外国人拒绝在英国工作——“几十个影响的故事”,高尔斯沃西说。
尽管高尔斯沃西在公投中处于失败的一方,但他认为他为科学家提供更大发言权的运动是成功的。他说,在2015年大选之前,科学不在政治议程上。“科学现在肯定是政治关注的焦点。”英国政府试图解决科学家的担忧,宣布到2020年每年为研究提供20亿英镑(25亿美元)的新资金,并保证对现有的欧盟研究拨款的支持,也到2020年,这可能会受到英国脱欧的威胁。
高尔斯沃西说,但更广泛地说,政府玷污了英国在国内外许多科学家眼中的形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么你就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这并没有减轻研究人员的担忧。
高尔斯沃西说:“这是对英国脱欧的伤害及其造成的分裂的加倍打击,并直接涉及科学界的身份认同。”“她很健忘。”
在英国退出欧盟的条款仍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他现在希望激励研究人员对英国和欧洲的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英国脱欧是对该地区作为全球科学中心角色的生存威胁——“除非我们能够足够聪明地避开这一点”。
现在不是学术界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
多米尼克·谢拉德,英国莱斯特德蒙特福特大学副校长

在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后的第二天早上,谢拉德在德蒙特福特大学召开了一次会议。一千人在接到通知几小时后就出现了。
“有很多非常痛苦的人,”他说。“有些工作人员泪流满面。一个波兰学生问我是否可以给他写信。我说:“你要信做什么?”他说,‘这个周末我要回波兰,我需要给希思罗机场的边防人员一封信,让他们让我回到这个国家。’”
和英国许多大学的副校长一样,谢拉德不希望英国脱离欧盟。与其他英国大学一样,他的教职员工、学生和研究经费中有相当大比例来自欧盟。在投票之后,大学部门一直因这三个因素都受到损害而紧张不安。
一些大学校长已经开始给报纸写信或发出保护请求,而谢拉德则发起了一项名为#爱国际的运动,以安抚现有的和潜在的欧盟教职员工和学生,并保护他们的居留权。
他的策略包括举行24小时守夜活动,以支持欧盟工作人员和学生,以及更广泛地反对全球的不容忍。谢拉德还访问了欧洲,在尼科西亚、华沙、斯德哥尔摩、维尔纽斯和柏林与有关人士交谈。
与学术界的许多人类似,谢拉德强调,大学需要在三个关键问题上获得确定性:居住在英国的欧盟国民的权利,欧盟学生在英国大学的地位,以及欧洲研究资金。然而,他怀疑,既然谈判已经开始,大学是否会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对象。
他向学术界传达的信息是:与其等着别人做什么,“你可以有所作为。”你可以参与。你不能感到无能为力。”

权利和权限
关于本文
引用本文
阿伯特,A.,卡拉威,E.,克雷西,D.。et al。英国脱欧如何改变8位研究人员的生活。自然543, 600-601(2017)。https://doi.org/10.1038/nature.2017.21714
发表:
发行日期:
DOI:https://doi.org/10.1038/nature.2017.21714
